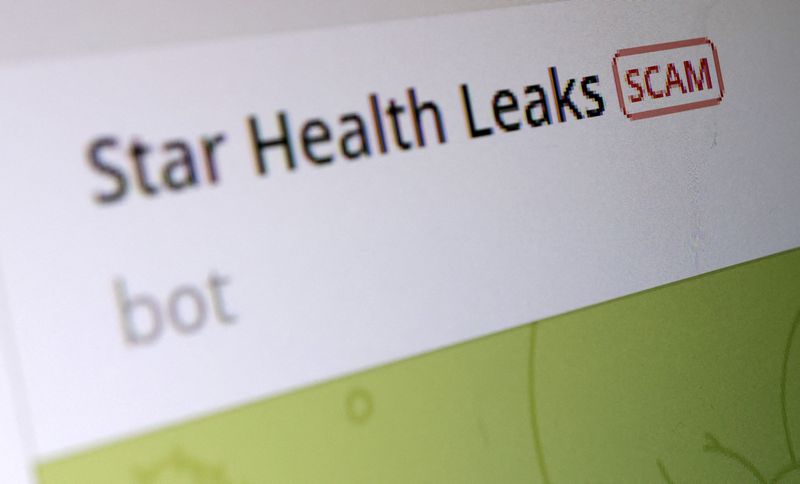在学校里,我总是被嘲笑为英国人,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英国人。我也是新教徒,而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做弥撒。由于我父亲的工作(都柏林切斯特贝蒂图书馆伊斯兰艺术策展人),我父母经常旅行,我们吃了不同的食物,所以我想我身上有一些“他者”的东西。直到1993年我23岁搬到纽约,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是爱尔兰人。当你离开自己的国家时,所有这些差异都会消失;纽约的爱尔兰人认为我是爱尔兰人。
我和其他爱尔兰人在东村的Siné咖啡馆闲逛,我在一家名为the Scratcher的爱尔兰酒吧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学会了锡笛,并真正地融入了传统音乐。我在成长过程中从未接触过爱尔兰文化的这一面。9/11事件后,我从纽约搬了回来。它改变了一切。人们来自一个恐惧的地方,我不想在那种氛围中抚养我的孩子。另外,我想种蔬菜,到外面去。但那是凯尔特之虎时代,都柏林不是我成长的地方。
我记得在克里拜访了一位朋友,开着一辆有15年历史的高尔夫车四处行驶,注意到路上的所有其他汽车都是都柏林车牌的大型SUV。过去,从美国回国的移民开着大车,盖着大房子,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盲人男孩:“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天感到非常羞愧。这种痛苦仍然在我心中升起。”在新窗户里打开。]
我真的很惊讶这里的嫉妒是多么阴险。
我当时的丈夫(音乐家Mark Geary)正在巴巴多斯录制一张专辑,他设法为我弄到了一张票,让我和他一起作为他的造型师去那里旅行。我记得我告诉人们,他们的反应让我很惊讶:“哦,我的上帝,你太棒了!”这是开玩笑说的,但里面有一丝嫉妒。在纽约,人们的反应会是:“这太神奇了,太棒了,度过一段难以置信的时光!”我认为嫉妒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它来自一个缺乏的地方,一种对没有足够的东西的恐惧。在纽约有很多。
我也认为互相照顾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文化。十年前,我搬回纽约住了几年,当我告诉那里的人我在爱尔兰领取了儿童津贴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纽约地铁上没有轮椅通道,也没有聋人签名的消息。我想,因为我年纪大了,有了年幼的孩子,我真的注意到了“适者生存”的心态。如果你在纽约的表现不好,有人会把你踢到路边,踩到你身上。21世纪初,我回到家时没有工作,所以我带着装满样品的行李箱开车去了爱尔兰各地的商店。
当时我没有进入室内设计,因为真的没有市场。人们在时尚上花钱,所以我设计并制作了围巾、皮带和一些衣服。我在Costume精品店遇到了特蕾西(塔克)——我在纽约认识她的哥哥——她买了我的一些作品,这真的为我打开了大门。尽管我曾在纽约为Donna Karan工作,但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一名时装设计师。我一直觉得自己像个骗子。然而,我始终对室内设计充满热爱。我母亲的品味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儿时的家令人惊叹,而且一切都是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成的。她喜欢逛古董店,每当发现有人偷东西,她都会尖叫着把车停下来。我会非常羞愧的。我喜欢爱尔兰的生活节奏。是的,我们都很忙,但这里不一样;这不是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的激烈竞争。你可以在花园里,游泳,散步——一切都在我们家门口。这是一个更温和、更可爱的步伐,我们真的需要坚持下去。
话虽如此,当我住在Westmeath时,我确实感到孤独,独自工作,远离人群。住在那里有很多值得喜欢的地方,但在都柏林靠近同龄人对我来说很合适。我喜欢与Dunnes Stores合作的一件事是,我周围有一个团队。这就是我工作得最好的方式。虽然我的父母很放荡不羁,但圣诞节在我们家很传统,他们总是有人留下来,有朋友来吃晚饭。我非常喜欢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总是和男孩们一起装饰这棵树;
几年后,我学会了让他们做,然后再回去收拾!我喜欢用各种配菜做圣诞晚餐,但我一年中最喜欢的一餐是斯蒂芬节。每个人都来找我,我确保有足够的冷火鸡和火腿,然后我把土豆、蔬菜和馅料放在烤箱里烤大约四个小时,直到它变成金黄色,形成一个华丽的外壳。我25岁的大儿子在过去两年一直在澳大利亚,他将于12月4日回家,所以今年将是一个重要的圣诞节。我等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