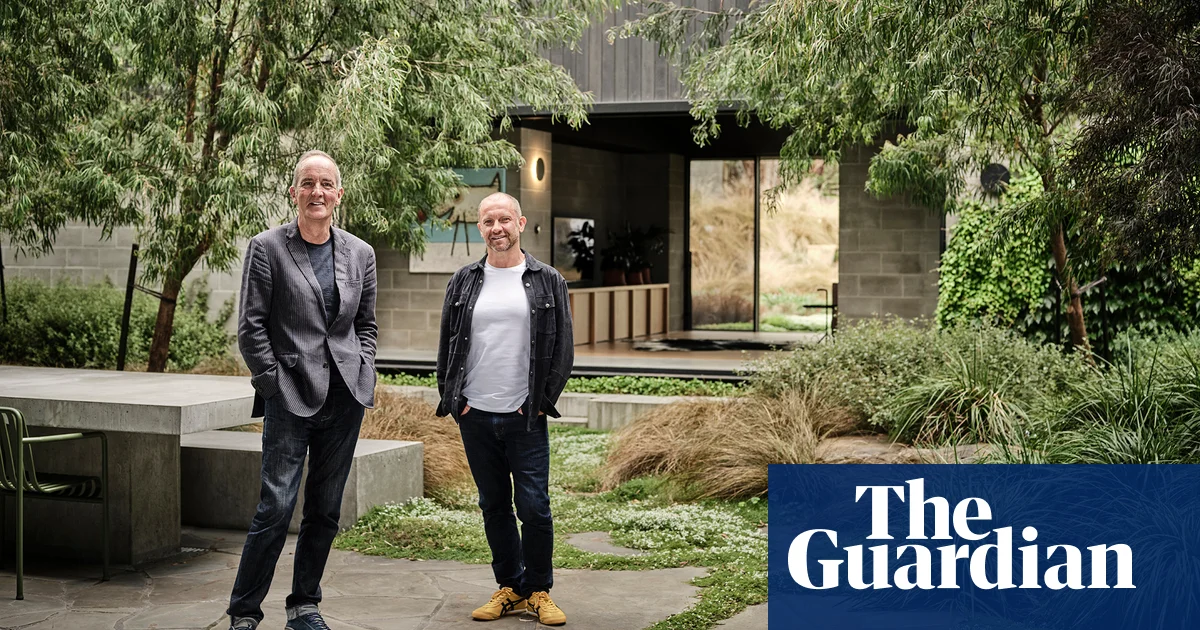安东尼·伯克深谙设计之道,也明白其重要性。这位悉尼科技大学的建筑教授是ABC《大设计澳大利亚》的主持人,他职业生涯中一直在研究和庆祝设计所能提供的最佳部分。因此,澳大利亚卫报请他谈谈自己在澳大利亚家庭设计中最厌恶的因素和最喜欢的特点,以及为何悉尼的新火车站令如此多人兴奋。在新澳大利亚住宅的趋势和功能方面,有什么最让你烦恼的?正是这些。过于重视潮流和功能而忽视基本原则。
大型开放式生活空间铺满地毯,卫生间比住户还要多,对表面而非实质的痴迷,建筑质量差,以及不努力与环境或背景相连接的房子,都是令我恼火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房子普遍太大;在设计上有点懒惰。通过削减大约20%的新建房屋,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我更希望看到个人化且独具特色的小型设计精致的房屋,而不是大空间。这对我来说,质量重于数量。我确实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在澳大利亚的房屋中,你看到哪些趋势让你感到兴奋?确实是这样。有两件特别让我兴奋的事情。首先是重新聚焦材料的环保性能。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古老的建筑技术如夯土和麻泥的重新应用,这改变了我们家居的质感和几何形态。此外,出于提升环保性能的需要,新材料在建筑中的应用也在增加。这两者都带来了对建筑工艺的重新关注,并需要重新思考建筑过程,因为它们并不典型。
不仅仅是快速搭建框架,而是倾注了关心和工艺,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当你看到、实际上是感受到一个精美制作的家时,你会知道。这种建筑工艺不需要大或炫耀,其实它存在,但很难找到。第二点虽然不太具体,但可能更重要。我真的觉得人们在寻找一种新的“家庭精神”来设计,这非常令人兴奋。很难确切说出,但我承认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我听到的不同版本是,一个家,无论是哪个家庭,都应该不仅仅是生活的务实手段。
在某种程度上,它应该能让你感觉良好;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道德上,或者是情感上。这可能与平静、安全或家庭有关,但有一种情感智力的设计感。在当前的住房危机中,当大多数人对任何屋顶都视为一种恩赐时,这很难谈论。但我们的家不仅仅是头上的一片瓦。而极致的建筑则是将平凡(比如做杯咖啡)升华为个人且非凡的东西,一种小小的仪式。建筑师和房主通过新能量的设计在寻找这种东西。
这可能是后新冠疫情的事情,但我感受到对我们家园意义的理解正在改变。澳大利亚的住房如何适应以在未来长期适居?这种适应快吗?这是个大问题。我认为我们目前也许正处于20年建筑实验和创新的起点,因为我们不能继续以常态进行。所以,外部对澳大利亚房屋的压力,比如生活成本、建筑成本、不同家庭形式的建筑(多代家庭、单亲家庭、老龄化人口)都在推动新思维。
我看到可持续性、变化的气候以及家庭办公的趋势要求我们必须真正改变对澳大利亚住房的思考。设计界正在做出回应。我已经看到可持续性几乎成为大多数房主谈话的中心——不是附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由于能源价格的推动还是责任感,这都是一个积极的重大变化。我看到澳大利亚住宅类型再次从典型的家庭住宅中扩大,迎来了多代同堂居住的形式,这是一种对小社区行动的庆祝(比如共享花园或自行车棚),这令人振奋。
这种适应正在进行中——也许还不够快,但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开拓者们都在为我们其他人解决这些问题。你认为卓越的住宅建筑的定义是什么?对我来说,卓越的住宅建筑是为住宅生活创造鼓舞人心的环境。最好的建筑能微妙地关注我们所重视的事物,其任务是凸显我们与自然、与彼此、与社区的关系,并将这些转化为每天体验的美丽事物。转换焦点,最近公众对悉尼新地铁的反应压倒性地积极。
这说明了公共建筑如何能让人有何种感受?
悉尼地铁取得了成功。是需求的满足、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的政治意志以及致力于超出实际考虑的质量设计方法的共同结果,产生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结果。这是一个重新规划城市的机会,为悉尼提供了一种新的积极市区空间,并更新了旧而熟悉的基础设施类型(地铁)。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对城市未来的承诺和对用户体验的关注让我们对集体前进的方向有更积极的感觉。
不知怎的,它捕捉了一种未来感,但将人心置于其核心,而不是房地产。我不禁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所需的项目。你最近是否记得悉尼(或任何澳大利亚大城市)对某项基础设施有如此一致积极的反应?我确实认为人们对环境的改变方式有很大期待,并且是的,大家想看到设计在公共领域开辟新途径。我们希望我们的共享空间令人兴奋,我认为我们正在重新探索城市的可能性,就像20世纪初、50年代初的态度一样,但这次是在气候和文化的压力下。
在公共建筑态度和投入方面,澳大利亚在国际上的表现如何?非常多样。我会说我们的住宅建筑做得很好,但在公共建筑方面仍然相对胆小。我们似乎在城市空间和景观设计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许在建筑方面,建筑师没有突破。设计在这个规模变得非常实际并且过分注重成本效益,使得对更广泛文化或社区利益的期望(无法在电子表格中度量的无形物)付出了代价。
可能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受到悉尼歌剧院经验的影响——一座真正非凡的世界级建筑,令所有参与方政治上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时的媒体报道全是关于成本超支、公共财政和谁该负责。这个政治教训50年后未被遗忘。因此,往往我们得到安全平庸的设计,实用但并不有趣,不是我们会因为受到启发而爱上的建筑。我能想到一些例外情况,但我们需要在澳大利亚对良好设计的公共利益有更多信心。我很乐观地认为地铁的成功将促进这种思维方式。